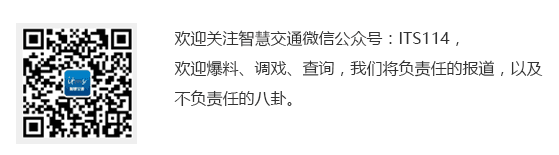“专车”怎么管?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顾大松/文
以移动互联网预约车特性来识别“专车”,目前在国内有两种形式:一是有许可准入的“专车”,其准确名称是“预约出租汽车”,源于交通运输部今年1月1日施行的《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4年第16号),目前已经形成雏形的是广州市交通主管部门即将推出的“如约”约租车。
二是交通运输部于1月8日肯定的、由市场自发形成的“专车”,其规范形式就是“租赁汽车+劳务派遣司机+网络平台”组合,而市场上最早的移动互联网预约车性质的“专车”,是快的公司2014年7月推出的“一号专车”。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专车规范发展问题,主要围绕上述两类形式专车展开,并分别将其称为“互联网专车”与“预约出租汽车”,以示区别。
“专车”的优质基因与先天不足
两类“专车”诞生,有自身的优质基因,同时也存在先天不足。
※。“互联网专车”蕴含的法治基因
交通运输部今年1月8日对中国交通新闻网记者表示,在中央主管部门层面,正式明确了“专车”的说法,也在发言中对“互联网专车”属性进行了高度概括,即“租赁汽车通过网络平台整合起来,并根据乘客意愿通过第三方劳务公司提供驾驶员服务”形成的创新。
正是在交通运输部这一政策意见鼓舞下,神州、一嗨等传统汽车租赁企业迅速推出“专车”业务,而滴滴、快的基于发展“专车”产品的需要宣布合并。人们将2014年称为“移动互联城市交通创新元年”。
上述“互联网专车”的法治逻辑就在于,由于目前的汽车租赁法规(主要是地方性法规),均明确规定“汽车租赁公司在提供汽车租赁业务时,不得提供代驾服务”,
而根据行政处罚法的处罚权法定原则,对于网络平台撮合的乘客向汽车租赁公司租车,向第三方代驾公司雇驾驶员形成的约车服务,主管部门对汽车租赁公司与第三方代驾公司,均无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也就是说,市场在法无禁止则自由的思维下,创造性地推出早期的商务车与后期的“互联网专车”产品,而政府部门基于“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肯定了“互联网专车”,在两者之间实现了“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的有机结合。这就是“互联网专车”自身所蕴含的优质法治基因。
※“互联网专车”的先天不足
“互联网专车”仍然存在诸多的先天不足,这些先天不足构成了当下“互联网专车”争议不断的根本原因。
首先,“互联网专车”所依托的租赁车资源市场化配置不足。得到交通主管部门肯定的合规“互联网专车”,其车源应当来自汽车租赁公司。但是,目前“互联网专车”发展最为集中、需求也最为旺盛的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均由于城市机动车限牌政策执行的系统需要,对租赁车源采取了行政配置方式,因此,本身源于市场创新推出的“互联网专车”,却又受困于租赁车源的行政配置,并不能真正实现市场对资源的决定性配置作用。
其次,“互联网专车”所依托的租赁车属性不明。交通运输部1月8日的发言中,在肯定合规“专车”的同时,也强调禁止私家车接入平台参与经营。但是私家车能否通过在租赁公司挂靠的方式,或者过户到租赁公司的方式做互联网专车呢?这又是当下“互联网专车”争议的核心问题。
在行政许可法放松管制的精神下,特别是近年国家大力简政放权的深化改革过程中,许多地方也不再立法设定汽车租赁许可,因此租赁汽车登记为营业性质也往往缺乏法规依据。许多城市私家车辆可以自由过户为租赁公司车辆,只是在车辆的登记属性上明确为“非营运”(也有少数城市只是注明“租赁车”)。因此,一旦立法将营运车辆作为从事预约用车业务的条件,就会将交通部所肯定的租赁车跨界创新服务之路封杀。
※“预约出租汽车”的优势与先天不足
预约出租汽车源于《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第五十三条规定,其法定地位清晰明确,这是其最明显的优势。因此,基于预约出租汽车与“互联网专车”均有预约用车的基本特性,可以将其称为“体制内专车”,相应地,“互联网专车”则可称为“体制外的预约出租汽车”。
然而,预约出租汽车仍然存在先天的不足。
首先,预约出租汽车的法律渊源有瑕疵。预约出租汽车许可作为交通运输部16号令中明确的行政许可,在形式上源自国务院2004年412号令《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第112项,即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核发”。
但是,2004年国务院保留的出租汽车许可,其历史含义是传统出租汽车属性(即在道路上通过巡游方式获取客源),而非与其具有本质区别的预约出租汽车(实质上,预约出租汽车的准确称呼为“约租车”,在国外行业分类中,与出租车处于并列而非包含关系)。
因此交通运输部以2004年国务院412号令行政法规为依据,并不能直接创设不同于传统出租汽车的预约出租汽车,根据行政许可设定的法律要求,部门规章设定行政许可必须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在这个意义上,16号令中新增加的预约出租汽车许可类型,并无上位法依据。
其次,预约出租许可条件与标准缺失。交通运输部2014年16号令涉及到出租汽车许可条件的条款集中在第8条、第9条,但均系针对传统出租汽车量身定做。因此,将预约出租汽车按照传统出租汽车条件实施许可,必然面临诸多难解的冲突。即使16号令施行已有半年左右,也没有城市正式开展预约出租汽车许可(去年11月7日,广州市只是召开了预约出租汽车运力投放听证会),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
需要城市治理框架下的“二选一”
由于两类形式的“专车”均存在先天的不足,甚至两类“专车”在同一城市并存时,因其均为预约用车性质,就会产生法律的冲突。
需要许可的预约出租汽车与市场已经形成的“互联网专车”在特性上基本一致,但后者却未取得主管部门发放的行政许可从事同一活动。因此,当取得预约出租汽车许可的公司与个人,以上述行政许可法规定为依据,要求主管部门查禁市场上已经存在的“互联网专车”,其中的矛盾就会凸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州市交委在交通运输部肯定“互联网专车”的次日(今年1月9日)还发文明确:目前各打车软件“专车”所使用的车辆、司机均不具备合法的客运营运资格,涉嫌非法营运,将依法严厉打击。而广州早在交通部2014年第16号令出台之前,就在筹划推出预约出租汽车,也率先于去年11月7日召开了“约租车”运力投放听证会。可以说,这里面就存在两类形式“专车”在法律上存在冲突的深层次原因。
因此,有必要以城市交通的地方性为依据,特别是依托城市政府制定的出租汽车发展规划,在发展预约出租汽车或者“互联网专车”之中进行“二选一”。
由于中国正大刀阔斧地进行以取消非许可审批、减少行政许可为代表的简政放权改革,所以,有必要从尊重市场创新的角度,选择发展“互联网专车”而不实施预约出租车许可,通过出行领域市场创新的典型——“专车”创新的引领,推动“全民创新”。
当然,在选择发展“互联网专车”的同时,也有必要将城市政府的意愿,通过及时制定出租汽车发展规划予以体现,即明确不实施预约出租汽车许可,以解决行政相对人申请预约出租汽车许可的标准不足问题,避免陷入行政不作为的争议。
规范发展的重点在于合作监管
秉着城市治理的精神,城市政府通过出租汽车规划确定不再发展预约出租汽车,而规范发展“互联网专车”,是国家深化行政审批改革精神的直接体现,也能将重心从准入管制转向事中事后监管,通过平台监管,公允分配平台的合理注意义务,创新信息规制方式,以实现合作监管。
首先,“互联网专车”的平台监管是基础。少数打车软件企业已经有着构建移动互联网交通一元化平台的足够雄心,有必要将其纳入信息产业范畴而非运输产业范畴,进而对其实施以信息规制为重心的事中事后监管。
其次,事中事后的信息监管以平台企业的合理注意义务原则。目前美欧日韩等相关立法均未要求互联网平台承担极为严格的责任,而是要求平台履行合理注意义务,根据过错承担相应责任。这样做的立法目的在于适应互联网特性,既能促进互联网产业发展,同时也能保护消费者权益。
最后,信息时代的问题应注重信息规制的转型。
移动互联网技术在“专车”领域的突出优点在于对信息不对称的改变,因此有必要重点使用信息规制工具开展“专车”的监管创新:一方面强化推出“专车”产品企业向主管部门的信息提供义务,不仅是“专车”车型、驾驶员信息、价格标准等要公开,同时也应包括约车人对“专车”服务的投诉信息,企业的投诉处理结果信息等。
另一方面,主管部门在掌握企业上述信息的情况下,在依法保护企业商业秘密与乘客个人隐私信息的同时,通过主动的信息公开机制,将企业未能履行相关准入标准、平台监管职责的事实,公之于众,让社会选择“专车”产品,进而实现互联网时代“专车”产品的信息规制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