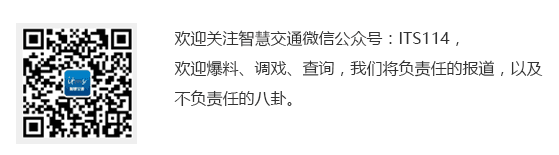中央立法还是地方立法?
专门的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立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层面的法律是缺失的,国务院层面的行政法规也是缺失的。原建设部2005年通过并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已经明显不适应需求:一是在规划、建设、维护、安全保护等方面依然是被法治遗忘的角落;二是随着2008年大部门体制改革的推进,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运营划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规章的执法主体难以适格。
由于中央立法的缺失,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些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的地方法规,例如广州市人大常委会2007年7月27日通过的《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布了一些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的地方规章,例如北京市人民政府2004年发布,2007年、2009年两次修改的《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管理办法》。
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立法到底是中央立法模式,还是地方立法模式?如果中央能统一立法,特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能通过专门的法律,这对于保障法治的统一性,满足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事业的需求,诚然是理想的立法模式。但必须看到:一是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事业从全国范围看才刚刚起步,需要地方积累立法经验;二是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依然是数量有限的大中城市的事务,不是全国城乡的普遍事务;三是中央立法往往受到部门职能的限制,交通运输部对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运营的职能是“指导”,实质性的管理职能属于地方性事务。基于此因,中央立法恐怕只能是在地方立法之后。现阶段的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立法仍然以地方性法规为主的立法模式。
行政立法还是行政民事兼顾立法?
地方性法规制定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方面政府的职责、政府有关部门的职责以及相互关系、政府、有关部门与相对人的行政法律关系,在立法权限上是不存在障碍的。但如果涉及本文开篇案例赔偿的民事问题,则是比较复杂的立法问题。
1999年10月1日实施的《合同法》中的运输合同是不包括城市公共交通的,但新《合同法》中运输合同是否调整城市交通包括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笔者曾就此专门请教过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有关人士,他们答复说“没有明确过,但也没有排除”。这主要是由于城市交通包括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很难用平等、等价有偿、自愿、公平这些合同原则对号入座,其公益性、民生性特点必然是财政大量补贴作为最终买单者。
《侵权责任法》于2010年7月1日实施,该法第9章高度危险责任第73条确定了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举证倒置及民事侵权责任;第77条确定了高度危险责任赔偿限额制度。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本意看,一是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的侵权责任属于民事赔偿;二是允许规定最高赔偿限额。
《立法法》规定民事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而地方性法规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笔者认为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是指《物权法》第136条:“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在土地的地表、地上或者地下分别设立。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的规定,已经为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建设用地的立体使用奠定基础,按照该法第246条:“法律、行政法规对不动产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作出规定前,地方性法规可以依照本法有关规定作出规定。”的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就此作出制度安排;“有所不为”,是指承担高度危险责任,规定赔偿限额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制定。
最终比较科学的立法应当是把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赔偿纳入国家赔偿、行政赔偿,而不是采用合同等方法解决。
全方位立法还是运营立法?
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的政府管理职能配置在各个主管部门,规划配置在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建设配置在住房和建设主管部门、运营配置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安全防恐配置给公安部门,这对于合理分配工作量、分部门实施提高效率是有益的,但在部门主导立法的体制下,给立法带来许多困难。无论中央立法,还是地方立法,由于主管事项体制不同,立法往往是给一个部门立法,这是造成许多地方立法只调整运营关系的主要原因。
一部法规只调整运营不调整前期规划、建设等问题,实际上是后期运营者法律责任加重,前期规划、建设者没有法律责任。从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的实践看,前期规划、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必然带到运营中,例如投资商建设后必然转为运营商,行政许可一般是在前期确定。如果法规只调整运营难以完成这种行政特许体制;再如前期站点规划如果不纳入法定的公共交通决策程序,必然把矛盾转嫁到运营阶段。
因此笔者建议应当是总则、规划、建设、安全(包括安全保护和运营安全)、运营、维护、应急、监督检查、法律责任,全方位立法。至于管理体制可以采取只规定有主管部门,不规定是哪个主管部门,这样为体制改革留下余地,不至于法规成为改革障碍。
政府行政执法还是企业行政执法?
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立法中一个绕不过的难题:对乘客违规行为的行政执法交给政府交通运输管理的行政机关,还是交给运营企业?前者无论在理论实践方面,还是在法律依据方面,都不存在任何争论,但矛盾的焦点是对随时发生的违规行为依靠政府交通运输管理的行政机关,需要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支撑,其后果是导致行政成本过高,如果没有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支撑则出现违法不纠。
交给运营企业,许多人提出《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主体:行政机关;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委托的事业组织。没有规定授权给企业,因此授权企业缺乏法律依据。
笔者认为:
第一,应当允许授权,理由为:一是法律虽然没有规定可以授权企业,但也没有规定不允许授权;二是国际上许多国家立法对公共交通运输企业是允许授权的;三是国内地方性法规已经开始有授权,例如《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已经授权。
第二,应当严格限制,限制在:一是范围限定涉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利益领域;二是程序一般主张先责令改正,再处罚;三是执法行为种类限定在行政命令、警告和小额罚款的行政处罚;四是行政强制措施限定在扣留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物品方面。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庭